为什么人家读书涨知识,你只长肉?
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吃的。鲁迅喜写绍兴酒配霉豆腐。汪曾祺写荸荠茨菇汤,写玉渊潭的蜂蜜。张北海的《侠隐》,半本都是小说都是李天然今日又穿上长衫,带上墨镜,跨上自行车去北京哪个饭馆吃饭。吃的是什么?剧情就开始往下走了。
为什么作家们都喜欢写食物?民以食为天,写吃的,就是写天下的事情。
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虽然是一本菜谱,食单上的一些菜谱至今仍然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可如果一条条读下去,你会发现这些菜谱不仅仅如此,语言里有些很俏皮可爱的比喻和他对权贵俗气的抨击。你仿佛不只是阅读一本简单的食物菜谱,而更多的是袁枚的一个形象——尖酸刻薄,鄙视权贵的可爱老头。
他厌恶餐桌上人家夹菜的习俗,将这种强人所难的行为称作是对人的“施暴”。还特意记录下一个很小的故事,用于讽刺这种习俗。你读完他的小故事,你会讶异于这本菜谱的妙趣横生,暗暗发笑。
以箸取菜,硬入人口,有类强奸,殊为可恶。长安有甚好请客而菜不佳者,一客问曰:“我与君算相好乎?”主人曰:“相好!”客跽而请曰:“果然相好,我有所求,必允许而后起。”主人惊问:“何求?”曰:“此后君家宴客,求免见招。”合坐为之大笑。
[自译:用筷子给客人夹菜,硬塞入(客人)口中,这种行为就像强奸,真是太可恶了。长安有个不会做菜但却喜欢请客的人。有一次请客人吃饭。客人问他:“我和你关系好吗?”,主人说:“很好!”客人跪坐在地上请求说,“要是真的关系好,我有事情求你,你必须答应我,我才起来。”主人非常惊讶地问他,“有什么事情相求?”客人说,“以后您家请客吃饭,求求您别再请我。”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。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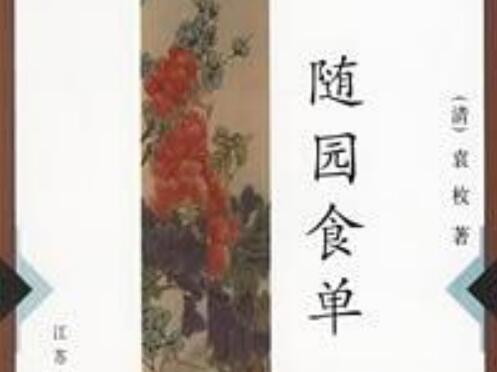
他认为厨师对食材随意处理太俗气,认为满汉全席太注重形式和排场俗气。对只认为吃海参、燕窝才好的人,他觉得是“庸陋之人也,全无性情”。他喜欢朴素的食物,但却一定要追求食物独特的味道,因此袁枚很有格调,他对自己的一些食物吃法洋洋得意。
往往见富贵人家,讲菜不讲饭,逐末忘本,真为可笑。
[自译:经常见到富贵人家,只注重菜肴的丰盛,而不论米饭的好坏,逐末忘本,真是太可笑了。]
十月天晴时,取芋子、芋头,晒之极干,放草中,勿使冻伤。春间煮食,有自然之甘。俗人不知。
[自译:十月份天晴时,取芋子、芋头,晒干晒透,放在草堆中,防止冻伤。等到春天煮来吃,有自然的甘甜。普通俗气的人怎么会知道这种吃法]
袁枚是乾隆时期的大才子,以性灵而著名。这本食单处处可见他对人们浪费食材的“吐槽”。他对食材追求“原味”与“新鲜”的极致,遇到平庸厨师大乱炖时,用幽默俏皮的语言表达这种无奈。
今见俗厨,动以鸡、鸭、猪、鹅,一汤同滚,遂令千手雷同,味同嚼蜡。吾恐鸡、猪、鹅、鸭有灵,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。
[自译:我现今见到平庸的厨师,将鸡、鸭、猪、鹅,放在一锅中滚煮,这使得所有的食材都只有一个味道,如同嚼蜡。我想如果这些家畜都通灵性,肯定要在枉死城里告(厨师)状不可。]
我阅读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时候,刚开始是好奇古人做菜的菜谱与现代人有什么不同,但很快就被袁枚的幽默文字吸引,在这些幽默之下,又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故事。读后感www.simayi.net一道菜,也许只是食物,也可能是一个故事。人们常常说“美食”,有时不仅仅是因为食物的味道鲜美,而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而发生的故事是让人感觉美好的回忆。
食物往往和人类的故事发生连接的时候才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。我读过一首最让我感慨的关于食物的诗是乐府诗里的那篇《十五从军征》。
十五从军征,八十始得归。
道逢乡里人:家中有阿谁?
遥看是君家,松柏冢累累。
兔从狗窦入,雉从梁上飞。
中庭生旅谷,井上生旅葵。
舂谷持作饭,采葵持作羹。
羹饭一时熟,不知贻阿谁!
出门东向看,泪落沾我衣。
这首诗的故事很完整,当年是选入我们的初中课本的,我一直能背诵。但是到这两年重读时,才觉得这首诗的悲悯和人道。
十五岁的少年从军,八十岁才归乡(那个七十古稀的年代,知道这个主人公已经是高寿了)回到家中一片颓败,杂草丛生,坟冢累累,野兔野鸡横窜。他采摘野谷、葵菜做饭,饭菜都熟了,但是也不知道该和谁共进晚餐。打开门,往东边看去,流下了眼泪。
这诗里提到了食物,提到了各种食材,可是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被战争所毁灭的军人和他的家庭。曾经年少出征还有家在故乡的希望,等到退伍归来时,才发现自己也白发苍苍,而且已经孑然一身了。这让我想起蒋兆和先生的作品《流民图》的悲悯。
但是这种悲悯的故事在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是看不到的。因为前面也提到了袁枚是一个性灵之人,是个老顽童。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康乾盛世。(他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,竟然大量传授女性诗文教育,这是当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。可见他的性格之洒脱与乐观。)他的食单里,有关于和尚不愿意教他做素面;有朋友家的月饼很好吃,他特意雇轿子将厨娘请来的小事情。他的个人的生活记录丰富了食单的趣味性。
我也试着模仿他写了一些自己的饮食记录,分享给友人看,自诩为美食理论家。这部分会在下一篇写道,这里不再展开。
袁枚写食物的事情对我很有启发性。他写笋。讲述天台僧人造笋油,后面又提到了一个定慧庵僧人做素面的记录。我对此在笔记上写了一个模仿《聊斋·促织》的小故事。
汴京曹门,一屠夫善解牛,解牛不下万头,人称之万解牛。
汴京干旱数月,一日,一白眉长须仙人骑青牛入曹门寺。仙人来此助雨。万解牛行经一片竹林,望见曹门寺外青牛。青颈黑角,脊背健硕。万解牛竟不能自持,提刀斫牛,解牛归家藏之。翌日,口生脓疮,再几日额生两角。汴京大夫均不知其所以然。万解牛奄息垂足。
白眉仙人化身云游比丘,过曹门万家乞食。万氏小妾遗金一两,白眉仙人:“多矣。”妾曰:“老爷有疾,恐不久于世,命妾厚仆众。”白眉仙人大笑,纳入百衲衣,绝尘而去。妾归万解牛之室,口竟不自知而曰:“汝之疾,非虫蛊,乃障也。曹门寺为僧,七七四十九天可消肿,再过四十九天疮可愈,以此角可消,命可保。”妾大惊。
万氏遂为曹门寺一僧人,因饭量颇大,为伙夫。曹门寺以素面闻。做素面,先一日将蘑菇蓬熬汁,定清,次日将笋熬汁,加面滚上。寺庙众僧人少食皆可果腹,万氏胃大如牛,不能饱。主持命其做竹油,笋十斤,蒸一日一夜,穿通其节,铺板上,如作豆腐法,上加一板压而榨之,使汁水流出,加炒盐一两,便是笋油。其笋晒干仍可作脯。万式食竹脯,果四十九天消肿,再过四十九天疮愈。体型愈加肥硕。
只额上两角不曾消,且愈发顽硬,刀削无用。过一年,万式采竹做笋油、素面。十五月圆夜,竹林白熠一片,竹节皆开花,万氏西归。僧人埋之于曹门竹林。白眉仙人翩然而至,曰:“万解牛,出!”一青牛从坟而出,青光荧荧,其身健硕,飘飘然。
白眉仙人骑牛而去。至此后五年,汴京风调雨顺。
这个故事是我在看到袁枚写僧人榨竹油时候的一个想法,在过了几段,又读到做素面的描述,遂写成,很满意这个故事。
袁枚的这本书仍然是有点不够“接地气”,这与他的身份有关。不过瑕不掩瑜,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对食物有前所未有追求热情的时代,吃什么已经很简单了,有时候吃的有格调,是不容易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