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乡土中国》有感3000字:
在那个充斥着对社会学是“剩余社会科学”的讥讽下,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仍然坚守着对这一学科的信心与信念。对于社会学的定义和对“边缘科学”的反驳,费孝通先生指出,“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、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。它只是从另外一个层次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。”毕竟与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独立的各个学科范围的局限认识相比,社会学则是脱离了这一局限,置身于外的方式,从不同的角度和递进的层次来看待同一个问题。用斯宾塞(Spencer)的话来说,“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,不应把社会学降和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。”
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所讲的是中国的“乡村社会学”,用社会学的角度,看待着转型期的新中国,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。通过比较社会学的方法,将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“个体”、“群体”,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、权力等等,进行比较,用特征进行描述区分,还乡土社会真正的面貌,现城乡冲突的内在问题。
《乡土中国》主要的视角定格在乡土身上,也就是农村。从个人的“愚”、“私”,扭转不同社会之间因不同的规则而产生的偏见。从个人与社区之间产生的“治”、“权”,探讨出城乡制度的不同之处的基本根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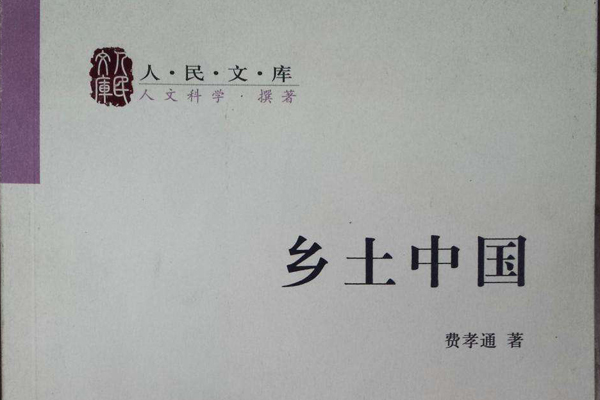
何为“愚”?城里人认为,“愚”体现在不识字、对新事物呆头呆脑、土里土气,但这是很片面性的贬义,如果这么说,乡下人对于城里人的看法可能是“奸”,当然由于发言权掌握在城市的手中,所以自然就一边倒的认为乡下人“愚”。事实上,只是所属的社会环境不同,而在乡土和城市这两种环境中,个人因受限于环境,只对自己身处的社区了解,而无法理解另一社区而已。就如对于因不识字而产生的文字下乡的政策,其实“在熟人中,我们话也少了,我们“眉目传情”,我们“指石为证”,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,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。所以在乡土社会中,不但文字是多余的,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卫衣象征体系。”所以,不识字根本不能认为是因为乡下人“愚”,而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,文字是多余的。而在以陌生人为主的城市社会,没有文字,则寸步难行。因为需要,所以精通,“愚”是相对的,任何人进入新的社区中,都会被土著称之为“愚”,事实上只不过是不明新社区的新规则罢了。(对于愚的观点,在《人论》中也有相近的观点。)
如果说,“愚”是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的产物,而“私”则是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的差别。西洋社会的“己”则是像“我们在田里捆柴,几根稻草束成一把,几把束成一扎,几扎束成一捆,几捆束成一挑。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、扎、把,非常的明确。”而在中国社会的“己”则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,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。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。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。”对于西洋社会的人情关系的重点就在于“权”,你处在哪一个层次的扎、把就决定了你的圈子如何。而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却是具有伸缩性的,随着你的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,故就有世态炎凉这一说,而红楼梦便是这一人情关系的一大现象。
正由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不同于西洋社会,所以当西洋社会争夺“权”而获得资格进入更高一层次的“束”时,中国社会则不断的通过攀关系,将自己的圈波及到更多的圈中,提升自我的中心势力,因为圈子的大小就取决于“私”,所以也就不得不将力作用在“私”上。因此,可以理解为何法律在中国社会推行的如此之艰难,正是因为其在制度上不适合以乡土社会为主的中国社会,就如文字下乡。而当中国社会慢慢转型为城市社会时,法律制度自然而然会被社会所接受,因为在陌生人社会,借条永远比信任来的可靠。
无论是“愚”,还是“私”,都是不同社会之间由于所需知识的不同,而产生的误解,而当误解产生时,势力上占优势的一方社会自然会以不屑的眼光,看待劣势社会,相应的用贬义的词汇去解释这一区别。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是极为幼稚的、无知的,它的产生同于井底之蛙,而造成的歧视后果则不堪设想,毕竟自认为是最优越的种族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是种族清洗政策。而如果从单一学科分析的话,便会造成难以跳出本社会的局限,但是如果用社会学的高度,就可以以各个社会为研究的单位,跳出囹圄,毕竟站得高看得远。
社会是由各型各色的人,在一定的规则下,组成的共同体。而选择怎样的规则进行限制,就决定了这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。这也就是,《乡土中国》所提及的“治”。“治”常认为两种,“人治”和“法治”。事实上,在乡土社会是不存在“人治”,因为因个人好恶的治理,之所以能统领大家,读后感www.simayi.net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不成文的规定,那就是“礼”。与其说是“人治”不如说是“礼治”。我国当今的目标,必定是建成法治社会,但是从另一方面讲,这便是乡土社会的消亡。而到底社会是需要礼治还是人治,则取决于社会变迁的速率和人口流动的数量。
当社会变迁过于迅速时,传统的、不成文的礼治是来不及应付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问题的。只有通过较为快速的法规制定(虽然也存在着法的滞后性,但相比在试错的过程中矫正,则显得更快),来应对社会变迁。当人口流动数量过大,那么不属于这一社区的陌生人急剧增多,带来的是不同社会的不同规矩,对原有的规矩的破坏和冲突,则会导致这一社区的不成文规定出现混乱,无法继续维护当前社会,所以就需要用文字规定的法条,来约束、管理来自不同社区的人。而当下中国之所以选择法治社会,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,社会变迁速率快,人口流动量大,自然原始的乡土社会中的礼治已经无法继续维护社会的秩序,法治道路这一选择,也就不言自明。
既然有了“治”,那么实现“治”必然需要“权”来执行。本书中的“权”分为四类,横暴权力,同意权力,时势权力,教化权力。横暴权力,从社会冲突方面着眼,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,权力是维持这种主从关系所必需的手段,具有压迫性质,有上下之分。同意权力,从社会合作方面着眼,由于社会分工使得每个人都不能“不求人”而生活。其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,是同意,权利与义务要相称。这两种“权”,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政府的管理,既有横暴权力的部分,也有同意权力的支持。但是这却无法应用到对于乡土社会的认识,就横暴权力而言,除非“乡霸”这一恶棍组织的出现,否则在乡土社会中,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压迫性质可言的;再同意权力而言,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,并不存在没有他人则不能生活的地步,所以这一权力也不适用于乡土社会,故“治”的实现,靠的既不是横暴权力,也不是同意权力。
而确切的说,乡土社会是一种长老统治,因为在礼治的规范下,在这一社会待的时间越长,对“礼”的知晓更为权威,也就更有发言权,所以长老统治成为了乡土社会的主要统治形式,而这一形式运用的则是教化权力,教化权力就是paternalism,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,同爸爸式的权力或称长老权力,是为了被教化者,而不是为了统治关系的“权”。这是在变迁不大的乡土社会中适用的统治方法,然而在社会变迁的速率加快时,由于教化权力的严重滞后,所以就产生了时势权力,也就是“时势造英雄”,这一权力的持有人,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,能获得别人的信任,可以支配其他的群众,并挑战、破坏长老统治。这正是近现代,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过程中,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,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也在不断的此消彼长中寻找平衡点。
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构建的“乡村社会学”,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文字,讲述着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,实在令人敬佩、叹服。或许把高深的问题讲明白,就是所谓的大家风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