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走的“父亲”——读《乡土中国》有感1000字:
曾几何时,中国家庭“严父慈母”的组合转变成了“虎妈猫爸”。这一转变中,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出走的“父亲”形象,一个从“乡土中国”出走,走到了现代社会的“父亲”形象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家庭,“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”,父亲作为一家之主,是事业的领导者,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显赫。但情感上却不如母子那么亲切了。长时间事业化的家庭管理,让父亲与家庭的关系趋近于陌生。
我认为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父亲与家庭趋于冷淡的根本原因。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缺乏流动性的。的确。它构成了稳定的社会:男女老少每天安居乐业,井然有序。“回到家,夫妇间合作顺利,个人好好地按着应做的事,各做各的。”人们根本找不到机会,也不想找机会交谈。这样,夫妇间的感情淡漠开来。而且,生育不过被看作功利性的任务。孩子不过是继承事业的工具。母亲仍然有较长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,而父亲以长辈的形态来教化孩子,又因为一家之主的光环,“父亲”这一形象逐渐的从人们的心中剥离而去,取而代之的是“大人”。在乡土社会下,父亲的地位明显的被抬高了,亲子关系变的不可亲近。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中描绘的父亲,强迫“我”背书,那不容反驳的语气,足以突出父亲在家中的权威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父亲贾政更是令贾宝玉闻声而噤若寒蝉;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在儿子们面前俨然就是一个霸道大boss。翻开一部部中国小说,鲜有以和善面目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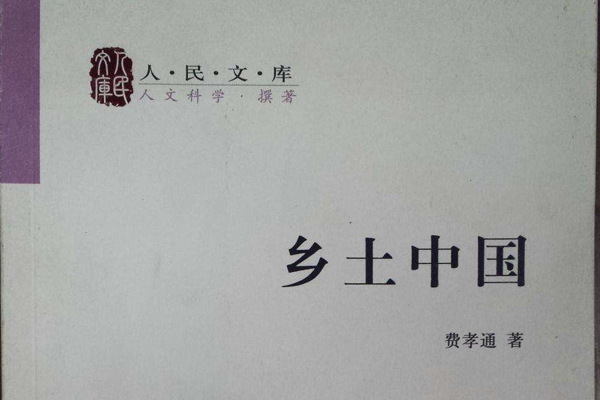
冷淡,是乡土社会父亲形象的一个标签;沉默寡言,则是这个标签外在色彩。朱自清在《匆匆》中描绘了一个沉默无言而又深爱着自己的父亲。他一次次用看似冷漠的背影,来抒写着对儿子的爱。刘亮程笔下的父亲更是一如耕牛般地存在于妻儿中,以致作者认为“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,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,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”。
但我认为这种关系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,乡土中国的确奠定了父亲与家庭关系的基调,但这种关系在乡土性逐渐稀释、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不断融合的背景下,变得缓和了。父亲与家庭的关系在变化。
舒已在《父子情》中写道“有一次,我要去东北出差,临行前向他(老舍)告别,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,我说带好了,他说:‘拿给我瞧瞧!’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,他才放心了。”老舍先生以他关切的问候,来表达他对舒己的爱。父爱,正在逐渐变得富于表达化,亲子之间相处的模式,也变得亲近化。走在大街上,随处可看到父亲牵着孩子的手,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去。父亲,正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融入孩子的生活中,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,暗中指引他前进的道路。
但严厉仍是父亲的标签,父亲赚钱,母亲养家的模式依然存在。我们只能说父亲的“出走”未能走出乡土性这块无形的领域,或者说,不能走出。但一次次“出走”,使得父亲这一形象逐渐步入正轨,使得他逐渐与我们心中的父亲重合。“出走”实则是异化的父亲形象的归位,归于慈祥,归于亲近。作者:何其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