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美丽新世界》被列为“反乌托邦三部曲”之一。相比于《一九八四》、《我们》,《美丽新世界》中人物似乎刻画的苍白无力,情节不够曲折。然而《美丽新世界》的特殊价值,恰恰与此紧密相关。
在“美丽新世界”,是体制(而不是人性)决定一切。在这里,“人”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,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。《一九八四》里无论温斯顿、茱莉亚,还是欧布莱恩,甚至“老大哥”,都还是人;《我们》里面的人物没有名字,只叫号码,但也是人;《美丽新世界》写的则是一个彻底非人的世界。
故事从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开始,从这里,你就已经能完完全全感受到新世界的“人”已经不再是人,仅是被设计出来的生命。从胚胎开始,人已经按等级划分,在不同环境中“孵育”,阿尔法胚胎享有最好的待遇,而德尔塔胚胎却不得不遭受酒精、射线、缺氧的折磨。在育婴室,婴儿被迫建立“书本和高昂的噪音”、“花朵和电击”的联结,以便他们不再喜欢书本和鲜花,而热衷于有利于社会的事物。同时,孩童们还需要接受催眠教学,让他们尊敬阿尔法,鄙视德尔塔,并让对自己的身份心满意足。
直到最后,孩童的心灵就是这些暗示,而这些暗示的总和也就是孩童的心灵。久而久之,这些暗示也就是成人的心灵。
“新世界”否认了与人性有关的一切,这里的人没有感情,他们没有家庭,没有丈夫与妻子,没有父母与孩子。人们认可情欲,对此习以为常,却认为感情是愚蠢的。
“新世界”中,人没有一刻能坐下来思考,人们忙着享乐,纵使碰到时间的隙缝,人们也会选择索麻,这种由我们看来,就是毒品的药物,备受新世界人们的追捧。“可口的索麻,半克就是半个假日,一克有一个周末,两克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东方旅行,三克是月球上黑暗的永恒;回来他们就发现自己在隙缝的另一边了,安全地站在日常工作和分心事物的坚实地面上。”
如此这般,没有感情、从不思考的“人”反倒才是被新世界所认可的。他们是服从的人、因满足而安定,头脑清晰的人,像车毂般稳定,这样的人才能够看管“新世界”社会运转的轮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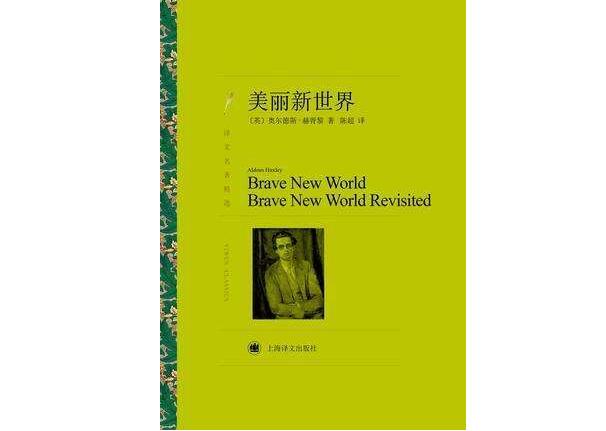
“新世界”的一切都是为社会服务的,在这里“自我”不存在,也毫无价值。
在新世界中,一切都是为了大我,人的价值在于对世界有用。他们活着的时候,为社会工作,死后,尸体则会被送到“泥沼火葬场”。火葬场四个高烟囱都有辉煌的泛光照耀,顶上还装有红色的警灯,这同时也是里程符号。烟囱上有阳台一般的建筑环绕,那是为了磷回收。气体在升上烟囱时要经过四道不同的工序。过去五氧化二磷都在人体烧化时流失了,现在其中98%都能回收。一个成年人的尸体能回收一公斤半以上,光是在英格兰每年回收的磷就多大400吨。亨利得意洋洋,为这种成绩衷心高兴。“真不错,想到我们死后还能继续对社会做贡献——帮助植物生长。”
这种极端的“有用”主义,让人毛骨悚然。
按理说柏纳·马克斯不应该在“美丽新世界”里出现。或许因为“人造血液中有酒精”导致柏纳体格不全,筋骨弱小使他与其他人隔绝孤立,他确实感觉到了孤独,造成了心智过剩。这使柏纳开始思考,他想要追求另一种方式的快乐,而不是从五岁就被灌输的“人人都快乐”,这种其他每个人都有的同一种方式的快乐。他希望自己能是更独立的,而不完全是社会的一部分,不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细胞。
不过,柏纳对既有的秩序的反抗,不过停留在发点牢骚罢了,他并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,甚至为了保全自己,不失时机将多年前在“保留区”走失的琳达和主任的儿子约翰带回“新世界”,一度成为红人,沾沾自喜。
与柏纳相比,他的好友汉姆荷兹更加高尚,他因为心智过剩而故意孤立而装聋作哑。他向柏纳告白:“我有时会有奇怪的感觉,觉得自己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——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而且我无法使用这股力量。如果有另一种写作方式……或者有另一些别的可写……”在与约翰认识后,汉姆荷兹找到了使用力量的方法,找到了写作另一种写作方式,最后,他作了一首关于孤独的诗。“个人有感受,组织就动摇。”汉姆荷兹也因此必须离开新世界,被送往冰岛。
“野人”约翰是这部作品中唯一的、真正的人,他是乌托邦社会之外的人,有着与新世界人们截然不同的价值观,导致“野人”与“文明人”之间冲突不断。然而身为外来者,面对从胚胎就开始的、根深蒂固的制约,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限。
虽然《美丽新世界》写的是非人世界,他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,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未来的期待。
“从一个盒子里放出来的好听的音乐,好玩的、好吃的。好喝的东西;在墙上一个东西上一按,就会发出亮光;还有图画,不光是看得见,而且还听得见,摸得着,闻得出;读后感www.simayi.net还有一种盒子,能够发出愉快的香味;还有山那么高的房子,粉红色的,绿色的,蓝色的,银灰色的。那儿每个人都非常快活,没有人会伤心或者生气。每个人都属于每个其他的人。还有那些盒子,在那儿你可以看见和听见世界那一边发生的事情,还有瓶子里的可爱的小婴儿——一切都那么干净,没有臭味,没有肮脏,人们从来不会孤独,大家在一起快快活活地过日子,像在这儿马尔佩斯开夏令舞会时一样。只是快活得多,而且每天都快活,每天都快活……”
这样的描写像极了乡村孩子对城市的向往。同样地,如果一个大城市的居民偏僻的乡村,相比也会如柏纳和雷宁那进入“保留区”一样惊讶并厌恶其落后、脏乱以及人们不加保养和修饰的皮肤。
《美丽新世界》的可怕之处在于,乌托邦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跟容易达到了。事实上,它似乎大步流星朝我们走来。
“幸福与美德的秘诀——乐为你所应为着。一切制约之目的皆在于:使得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。”这是敦孵育暨制约中心主任说的话。但这样类似的说法我们也听过无数次:“热爱学习”、“热爱工作”、“不能将你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视为负担,而要主动地、认真的、毫无怨言的完成这一切”。
除了忙于工作,我们也难以闲下来,为了寻找刺激,人们不断用各种无所谓的东西充塞大脑和心灵。为了打发时间,人们可谓毫不挑剔,饥不择食地追求五花八门的社交,消遣和享乐。
“美丽新世界”是温柔的怪兽,在“新世界”的制度下并没有传统的“残忍”,给柏纳等人的惩罚仅仅是把他们送到冰岛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其实是对他们的褒奖,因为冰岛上,都是和他们同样是指过剩的人,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生活。
“美丽新世界”的可怕在于其将快乐作为人类的至高追求。即使最高元首清清楚楚明白“真实的快乐,比起对悲苦过度补偿的快乐来,往往显得十分污秽。安定似乎及不上不安定那么悲壮。心满意足就没有了狠战不幸的那份迷人,也没有了抗拒诱惑、抗拒被热情或疑惧颠覆致命的那份生动。快乐永不伟大。”但他仍把快乐至于至高无上,无法撼动的地位。为了快乐,人们将科学、艺术作为代价付出。在“美丽新世界”,《奥赛罗》不可能被写出,也不可能被接受。就像没有钢铁就造不出汽车,没有不安定的社会和悲痛就造不出伟大的悲剧。
要反抗新世界是很难的,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在要求“不快乐”的权利,同时要求变老、变丑的权利,要求罹患疾病和癌症的权利,要求时时为着不可知的明日而忧虑的权利,要求为各种难言的痛楚折磨的权利,要求犯罪和成为受害者的权利……
在“舒服”和“不快乐”之间,人们很容易作出自己的选择。
叔本华曾说过:“生活就像钟摆一般,在两端之间或激烈或温和地来回摆动——要么痛苦,要么无聊。”这个世界绝不会慷慨无私,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很少。生活本充满了痛苦与不幸,就算你侥幸逃脱,无聊也会无孔不入,即可找上你。命运是残酷的,人类是可怜的。“美丽新世界”能够实现,规避了一切不幸与痛苦,此时人便永远处于无尽的无聊与怠倦的一端。对生活不再有任何期待的“人”,此时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