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了白先勇老师的《孽子》,在电脑前面坐了良久,仍感到意难平。我读书的时候最愿意跟朋友唠叨。书陆陆续续地读了三天,感慨的话也从“好一淋漓尽致的爱情群像啊!”变成恚然不平的一声“苦哇—”,脑海里都是《游西湖》折子戏《鬼怨》里饱满的秦腔。
再读到后来,倾吐的欲望一下子被遏住了。我跟着李青,看他目睹傅老爷子下葬,看他跟王夔龙握了手相继远去,又不免想起了韩缜《凤箫吟》里那句“长行长在眼,更重重,远水孤云。”郭公公说这群鸟儿终究还是会飞回来的,飞回莲花池边那一个隐秘国度,我却在这公园里读出了一层转瞬即逝又世代永存的双关来。李青是小苍鹰啊。虽不及鹰隼之凶猛(也是被世事和情字磨平了棱角),但也不愿鸳鸯似地与谁比翼而栖。荒谬的是,我等本是陌路人,却由一个共同的“孽因”聚在一起,擦出火花,把一本该平淡的人生映地轰轰烈烈。你说我该谢这社会还是不谢,怨这世故还是不怨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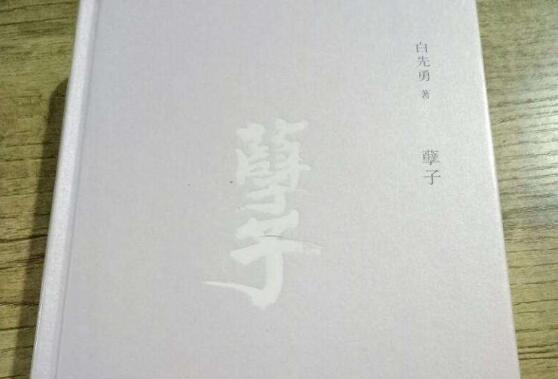
欧洲读者品《孽子》,看出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巴洛克歌剧。我却像看布莱希特的戏剧,越看画外音越前置,越看越清醒。倒也不必刻意去把哪一个人物“英雄化”。这书中本是一个个“我”,一个个“你”,一个个“他”。当你觉得诧异了,觉得悲悯了,就该赶紧把急于翻页的手收住,责问自己这一“异感”的来由。我模模糊糊地把这群“鸟儿”分了个类。一群人,想要的各不一,活的姿态也大相径庭。有背着标签找寻自我的(李青、阿凤);有带着旧愿渴望救赎的(王夔龙、傅老先生,李青也是);也有为欲所困一意孤行的(老鼠、吴敏、小玉)。
这三个类别好像三张不那么透明的网。有人身上罩地层层叠叠,便羁系终生。有人只罩一层,看世事也澄明些,但免不了一辈子束手束脚。白先生刻画李青,似是硬要在这荒诞现实中竖起一把尺子。他算是一群异类中最标准的,怪异得通情达理,庸常得畏首畏尾,自私而又纯良,知世故而又不世故。白老先生也谈父子情。书中多得是,二人说戗了,各自的流离与苦厄也开始了。我不知道李青读《大熊岭恩仇记》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。反正越是亲密越容易囿于成见,越是珍重越容易口不择言。最后你对着别人的儿,他望着别人的父,眼前人不是心中人,眼前人好似心中人,相互依靠着又孤单着落拓。谁也不知道李青最后有去探望他父亲没有,如果没有,也终究一辈子在别的长者身上找寻父亲的影子,在别的孩童笑颜间想起那一把口琴。
《孽子》群像|来源于网络
三水街的花仔最后唱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,就记得他曾经哼过《三声无奈》。我找来邓丽君老师唱的听了,歌声酽酽。“三声无奈哭悲哀,月娘敢知阮心内。”听着听着,读后感www.simayi.net白老师的文字像掩了一层悲情的滤镜一样。说来也怪,他写得愈平淡,我愈愕然。他愈笑看,我愈难平。倒也不是平淡中出英雄,我固执地认为这本书里没有谁是真真正正的英雄。只是他们活得太真了,在这社会破败的条框里还那样真,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自愧不如的崇敬与感慨。人世间的最大悲哀便是像傅老先生一般,对一切苦痛冰然、无动于衷。但看着《孽子》不明不白的最后一行字,我却在肖想着,在痛过以后,这世间一定也会郁郁葱葱地生出许多迷人的灵魂,在这冰面上肆意盎然。
我不敢说白老师有最宏大的格局,但他一定有最敏感的神经。
我是因为“标签”二字拿起的这本书。读罢,全然忘了“标签”这回事。倏忽想起自己最初阅读的动因,竟也隐隐地愧疚起来,倒觉得自己看低了这群人,看低了这本书。
